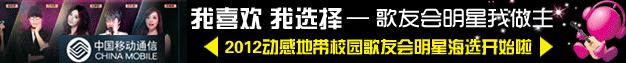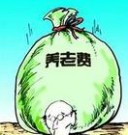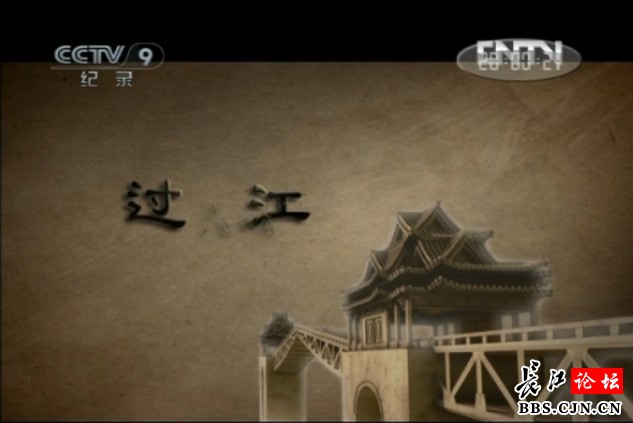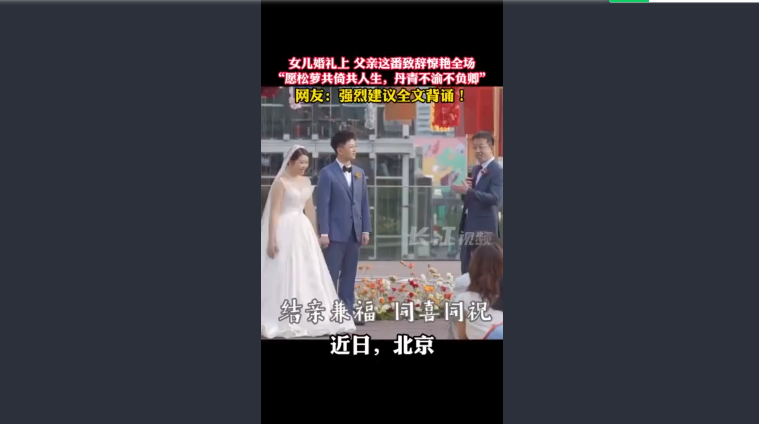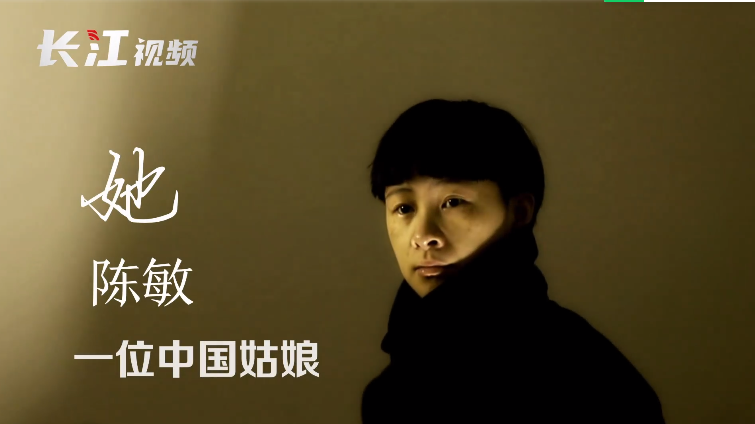樱花作为一种美丽的花,倘若没有什么内涵意义在里面,估计不会引发什么争议;倘若樱花生的不美丽不惹人注意,估计也不会引发什么争议。现在的问题是,樱花,既是一种美丽的花,又被日本定位为自己的国花;具体到武大樱花,它又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所以,每到武大樱花盛开时节,有关武大樱花的争论总是炒得沸沸扬扬。
激进一些的观点认为,武大的樱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耻辱,应该铲除;保守一点的观点认为,樱花只是花而已,不应该把赏樱这种艺术欣赏活动与民族仇恨情绪扯到一起。今年的争论似乎尤为激烈,网易“新闻PK台”甚至也推出了一期“武汉大学的樱花是国耻么”的专题,但结果也没争论出个所以然来。
实际上自从武大有樱花以来,关于樱花是铲除还是保留的争议就一直没停止过。鉴于很多人并不知晓武大樱花的来历,我认为在这里诚有先交代下武大樱花来历的必要。1938年10月,武汉三镇沦陷;作为一处风景秀丽的所在,国立武汉大学被日军辟为中原司令部和伤兵疗养处。1939年,为缓解这里日本军人的思乡之情,日军将从日本移植的樱花种在老斋舍前。日军这一举措,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要长期占领武汉。从这一历史来源来看,武大樱花是日军侵华的罪证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象征是毋庸质疑的,主张铲除樱花的人也是基于这个理由。
但这里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同样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象征,为什么圆明园我们要竭力保持原貌,而武大的樱花就必须废除?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民族心态:圆明园作为一处惨遭侵略者蹂躏而不堪入目的遗址,可以激发青少年的爱国斗志;而武大樱花作为一种侵略者带来的声色犬马之物,则会消磨掉人的斗志——不论我们如何借樱花盛开时节进行爱国宣传。这后一种心态主要是基于对“糖衣炮弹”的恐惧,害怕由观赏樱花而导致对日本产生价值认同而导致爱国立场丧失,而这正是大多数激进者所持有的。
由樱花的美丽和激进者的心态,我不由地想到了“美人计”。倘若放在《三十六计》中,上述心态正是对“美人计”的畏惧和恐慌。“美人计”其策为:“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将弱兵颓,其势自萎。利用御寇,顺相保也。”在“美人计”这一词构成中,“美”乃动词,“人”则只指敌人。“美人计”最初含义系指利用物质诱惑使敌人沉湎于淫逸享乐之中,后来才慢慢演化为利用美色达到粉碎敌人的目的。通常认为,在历史案例中“美人计”以春秋时越王勾践借西施美色灭吴最具有代表性。
单纯从美的角度而言,樱花和美女无疑是有一致性的,都可以使人赏心悦目。但倘若放到政治领域和历史领域,这二者能发挥多大的效用,我想任何人都不能妄下断语。依照事物发生变化的内外因关系,“女人祸国论”的哲学逻辑已经占不住脚;而过度担忧观赏樱花会陷入敌人迷惑的圈套,也委实没有必要。实际上对于这点,〈三国演义〉中刘备使孙权“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故事,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表率。所以,那些持激进态度的人的恐惧和担忧,既是狭隘民族主义在作祟,也是内心发虚的表征。
对于樱花之类的外来之物,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鲁迅先生早已做过说明。1934年6月7日,他在〈中华日报〉上发表的〈拿来主义〉明确指出:“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示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
对于鸦片鲁迅都建议我们以“拿来”的态度对待之,对于今天的几树樱花也无须横加鞭挞。何况当年日军种植的第一批樱花已经于上世纪50年代基本死绝,如今武大樱花大道上的樱花已经是原种的第二代、第三代。今天武大的樱花,已经不再是日本国度的一个意象,而是演化成了武大的一处人文景观。赏樱花者只是把它当作风景观之,很少有人会把它当作日本来膜拜。
当然,国耻我们还是要记住的。但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炎黄子孙,尚不至于因为看了樱花就做叛国贼;能做叛国贼的,也决不是因为看到了樱花。
物的属性都是人们赋予的,关键是我们以怎样的心态对待。
(责任编辑: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