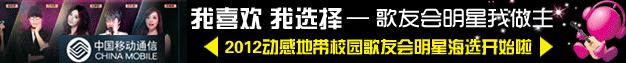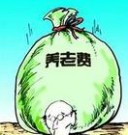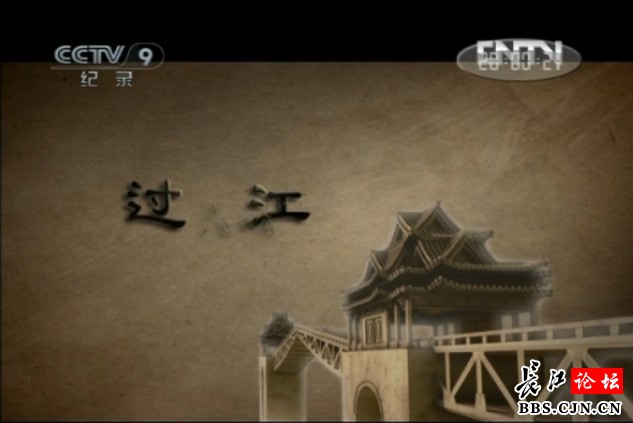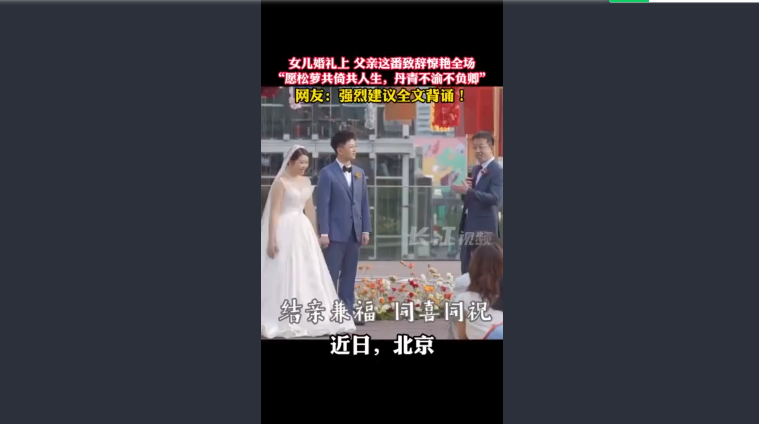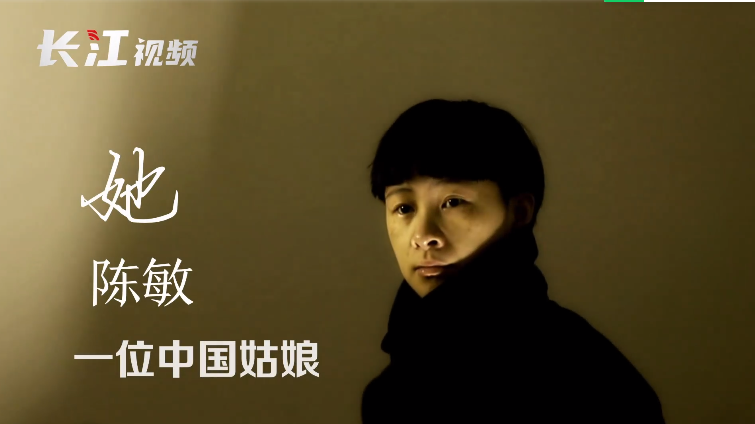由于曾经同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缘故,我国的文学界对苏俄作家总是非常有亲近感。其中自然有名不副实之辈,但绝不会是契诃夫。一向给人冷峻之感的契诃夫其实有两支笔,一支是无情地嘲讽,如《套中人》《变色龙》;另一支则充满了同情与恋爱,如《哀伤》、《苦恼》,我最喜欢的《万卡》正属此类。小说同样非常短,但在谋篇布局上却匠心独运。文中涉及的人物只有三个,万卡是作为唯一的叙述者出现的,他承担着书信体的任务。躲在暗处还有两人,一个是乡下的爷爷,一个是鞋店的老板,这两位角色始终贯穿于叙述当中,但在客观的限制上一直没有露面,但作为读者却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各自所代表的意义。这样的处理无疑大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层次感,并在无形中拓宽了小说的容量,产生了无与伦比的距离美。即使抛开一切的文学专用术语,就万卡脆弱的童真而言,小说也同样感人肺腑。
高中语文课本里面有许多我的私藏,栗良平地《一碗阳春面》就是其中之一。在那个容易伤感的年龄,每每阅读我的眼眶都会湿润,难为那时的我身为语文课代表还要在早读课上领读。对于这样一篇以情动人的作品,或许有人会觉得幼稚、矫情之类,但我同意北大曹文轩教授的说法,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感动?曹文轩教授认为现在的孩子存在感情危机,缺少同情心,不会感动,跟他们从小阅读的东西有着极大的关系,对此我深有感触,被《火影忍者》《死神》浇灌的孩子是怎样的一副德性我再清楚不过了。他希望从小培养孩子阅读有道义感的作品,以此耳濡目染地帮助孩子学会感动。这又让我想起了钱锺書先生《读〈伊索寓言〉》一文中的句子:“卢梭认为寓言要不得,因为它把淳朴的小孩教得复杂了,失去了天真,所以要不得。我以为寓言要不得,因为它把淳朴的小孩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分别、善恶果报也像在禽兽里一样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这似乎唱的又是一个反调。但请别忘了,钱锺書先生的最终结论是:“小孩子该不该读寓言,全看我们成年人在造一个什么世界、一个什么社会给小孩子长大了来过活。”而读《一碗阳春面》是否应该感动,全看你自己是怎样看这个社会的。
我的初衷是希望做一个全新的选本与大家分享,但个人阅读经验实在是有限,绕来绕去还是那一堆名篇。欧·亨利是我非常喜爱的名家,他的幽默不是文人式的尖酸刻薄,而是宗教式、福音式的广博。他在诙谐当中充满对社会底层的怜悯,且并非是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带有传教士般的诚恳。《麦琪的礼物》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拥有一贯的温情脉脉,及典型的“欧·亨利式的结尾”,最适宜情人间的朗诵。如果我是朗读者的话,一定会给汉娜念这个的。
同时期的美国作家我还喜欢杰克·伦敦,《一块牛排》是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许多好事者将他称作“体育小说”,还和他的另外一篇《墨西哥人》放在一起,真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中西比较文学中最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的小说重情节,而欧美的小说重细节,具体的体现是国外的文学作品中个人心里描写都很细腻,而这一特点在《一块牛排》中表现的是淋漓尽致的。杰克·伦敦那抽丝剥茧般的叙述,在一个接一个的Round中将曾经叱咤风云的老拳击手残酷地击溃。这结局似乎是早已注定的,途中的一切仿佛只是一次命运的轮回,把失败归结于一块牛排上也是这样的无可奈何。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傻瓜。《傻瓜吉姆佩尔》是我四年前读到的作品,当时我并不知道作者是何方神圣,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读着它,以致在数年之后我读到余华的一篇《我胆小如鼠》立即百分之一百二十地确定此乃模仿辛格的习作,经考证果真如此。作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犹太作家,辛格刻画人物的韧劲早已被大家所熟知,他从不借助别的辅助手段,而是往硬生生地往死里写,最终把人物写活了。诺贝尔评委称他是“充满激情的叙事艺术,不仅扎根于犹太血统的波兰人的文化传统中,而且反映和描绘了人类的普遍处境”,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辛格对犹太传统的继承,不仅是形式上的用古老的意第绪语写作,更重要的是他在叙述的过程中将犹太民族的命运漂泊感融入了人物性格当中,使得读者不由地对他的作品充满崇敬。我们甚至可以说,吉姆佩尔便是犹太人善良、勤劳、诚恳却又不断经历坎坷的民族形象,如圣徒般的纯洁。
在过去,小说的地位一直不如诗歌,因此批评家才会在评价某部时间跨度长、空间跨度大、出场人物关系复杂的长篇小说的时候形容它有“史诗品格”。但诺贝尔奖得主来自冰岛的拉克司内斯却用他的短篇《青鱼》告诉了人们,史诗品格与篇幅无关,只与作品的魂魄惊魂有关。这一位来自冰天雪地之处的作家“以生动的史诗气魄复兴了冰岛的伟大叙事艺术”,他笔下呈现的渔村是那样地一尘不染,仿佛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中。还有那一位如着魔般的老妪,由始至终都被神圣的光环围绕着,被儿子强行拖走的时候让人感觉一阵莫名的悸动。如果你是四个肉丝的歌迷,那一定会喜欢这部同样迷人的《青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