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照着西方给的单子去读书
作者:长江网记者李煦

郑若麟作客长江日报云端大讲堂。 长江网记者陈亮 摄
上周五,文汇报高级记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应邀来到长江日报“云端大讲堂”,结合自己驻法20余年工作,用亲身见闻和观察思考讲述“理性看待西方”,并接受了长江日报《读+》专访。
想在巴黎找一件“中国制造”
郑若麟与法国有某种缘分,这可以追溯到他的父亲郑永慧先生。郑先生是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翻译了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莫泊桑、福楼拜、梅里美、乔治·桑、萨特、罗伯·格里耶等人的数十部作品,其中雨果的《九三年》被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名著名译”丛书,被多次重印出版。
郑若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成长,1985年他第一次出国,来到法国。当时他在国内的工资是56元人民币,这是大学毕业后在北京的工资标准,人民币当时与法国法郎的兑换率是1.2:1,56元约合47法郎。他到法国后非常吃惊地看到,当时法国的最低平均工资是4400多法郎。
当时他乘车从巴黎机场到市区,一路上到处都是日本电器产品的广告,他就想在巴黎找一件“中国制造”。后来,他在奥斯曼大街的春天百货商店里找到一件“中国制造”,是上海生产的一个小玩具钢琴,价格正好是47法郎。
回忆起当年的冲击和震撼,郑若麟不禁感叹:“可惜我没有把这架小玩具钢琴买下来作个纪念。在那个年代,47法郎对我来说也已经是一笔巨款。”
渐渐发现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误读
初来乍到,遭遇到这样的思想冲击,郑若麟决心要把西方的先进文明观念带回国内,让祖国也能变得这样繁荣富强。他写了不少这样的稿子,得了不少的奖。
可是渐渐地他发现,西方文明对于“后来者”的“规训”与“教诲”,与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有很大反差的;他们富强的真实秘诀决不轻易示人,而他们挂在口边上的那套美丽说辞,常常会让人信以为真。
他在书中写道:“我们应该承认,长期以来,我们的知识分子实在是过于天真了。我们将西方有意识地传递给我们的一切当作了西方的全部,而对西方刻意潜藏的另一套实质性的行事方式和游戏规则,我们却一无所知。因为我们没有参透,西方从19世纪以来,就已经精心构筑了一套针对中国的话语,以此从精神层面主导、诱导中国大量文化精英在不知不觉中追随西方或国际舆论来认识世界、认识西方,甚至认识我们自己。甚至连我们最著名的西学大师如胡适、钱钟书(还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字)……尽管在他们各自的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真正认知西方文明的实质与内涵包括其历史、文化和宗教等上层建筑领域,却都令人遗憾地停留在门槛上,而没有跨出决定性的一步。”
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误读。
这方面郑若麟可以举出很多事例。比如在各种论战中常常出现的那句伏尔泰名言:“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郑若麟是第一个报道此话并非出自伏尔泰的中国媒体人,并且他还写出伏尔泰本人并没有这样的心胸。
他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后引来一批人反驳,还有人说:“哪怕这话是个叫花子说的,我们也还是赞成。”
郑若麟只好再撰文,说明法国有11.8万条法律,非专业人士很难搞清法律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不过有几点是明显的:1.如果在公共场合说“亚美尼亚人没有遭遇过种族灭绝”,那就是违法;2.他拿中文网络上常见的“找人弄死你”等话语咨询过法国司法界人士,对方回答这在法国都是违法,是口头煽动暴力;3.公布名人的车牌号、门牌号、性取向是违法;4.有人与警察争吵时说了一句“你怎么像维希的警察”就被判罚款,维希政府是“法国的汪精卫政权”,说这话就是犯了“侮辱公务人员罪”。在法国很容易触犯该罪,因为法国法庭视警察的话为宣过誓的可靠证词,所以与警察斗嘴、争吵很危险。
郑若麟的结论是,在法国公共场合,人们说话都很自律,尽量避免涉及种族、暴力、隐私、诽谤的言论,久而久之,就显得“文明”了;所谓“誓死捍卫说话的权利”,真相不过如此。
写了多本专著,呼吁国人理性看待西方
郑若麟的妻子、旅法作家边芹讲过一个故事:上世纪90年代初,一位驻联合国外交官夫人带来一个女孩——浙江来的数学系研究生,边芹陪她们一起去巴黎最大的百货店。“在电梯里,我问女孩:数学硕士的头脑有什么打算?她很干脆:留下来。哪怕永远离开数字去餐馆洗碗?我追问。她点头并把眼睛投向外交官夫人。此时我们已经走出电梯,眼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外交官夫人指着满堂财富反问我:那还用问吗?”
对此,边芹写了这样一句话:“你要什么”悄悄地决定了“你是什么”。
如今郑若麟夫妇都已退休回国,但是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仍然令他们感到忧虑:在一些豪华大型商场,很多店名都是用外文来标明;很多中国商品的广告,邀请的却是外国模特;电视台转播体育比赛,对外国运动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娓娓道来,崇拜之情溢于言表,甚至专门热衷介绍外国的强项,而对中国占优的项目常常三言两语一带而过;出国、外嫁仍然是被人羡慕的人生选择;很多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常常把外国当天堂……
郑若麟说:“我在外国生活了20多年,深知外国确实有很多比我们好的地方,有比我们发达、先进、干净、寂静、舒适、遵守规则的地方,但外国绝非天堂,离天堂还远着呢。”
郑若麟认为,“精神殖民”现象,不止存在于普通大众,还渗透到了大中小学教育,乃至一部分官员身上。他和边芹为此写了多本专著,呼吁国人理性看待西方。
【访谈】
我亲眼目睹 诺曼底登陆战被西方媒体无限夸大
读+:在您看来,我们普通人对于西方的认识,有哪些误区?
郑若麟:我们经常说西方是三权分立,司法、立法、行政。但是西方真正的三权分立,是资本、政权和媒体。媒体在西方是一大权力机构,其权力之大,大到超乎我们的想象。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大家的信息来源主要就是媒体。媒体每天给你描述你生存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它的价值在哪里。可以说,是媒体给我们塑造了一个“现实”。
媒体另一个作用就是塑造历史。大概1995年开始,法国外交部邀请我去参加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我也去了。当时法国媒体开始大规模地报道对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活动。我亲眼目睹了法国和西方主流媒体是如何在长达十几天的时间里,反反复复、连篇累牍地报道诺曼底登陆的。2004年诺曼底登陆纪念达到当时的历史巅峰:法国总统希拉克请来了几乎所有西方主要大国的国家元首,甚至包括德国总理施罗德,以历史性的大和解来强化诺曼底战役在二战中的地位。而与此同时,对斯大林格勒战役、莫斯科保卫战等真正在历史上起到转折点作用的报道却几乎是零。在这种报道方式下,普通民众的历史观不被改变才怪呢。
据法国IFOP民意测验机构所作的调查显示,在问“二战中你认为哪个国家对战胜纳粹德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时,1945年时57%的法国人认为是苏联、20%的人认为是美国、12%的人认为是英国。然而2015年同样一个问题,却有54%的法国人认为是美国,只有23%的人认为是苏联,以及18%的人认为是英国。70年间,历史竟被彻底改变了模样!
本来这个问题是不应该有任何疑问的。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了解,在整个二战期间,德军约60%至79%的主力一直在东线战场;而战争的转折点也绝对不是诺曼底而是斯大林格勒。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在他的畅销书《第三帝国的兴亡》里甚至根本没有为诺曼底登陆花费更多的笔墨,而只是一笔带过。
然而历史走到今天却被偷偷地改写了。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选择性的新闻报道对法国人进行深入、持续的“洗脑”。
戛纳电影节的日本电影充满温情 中国大陆入选片则完全相反
读+:在您的书中,在边芹女士的书中,对西方电影节的操作手法有具体讲解,这都是你们的切身经验吗?
郑若麟:这是我们旅居法国20多年的切身体验。
边芹多次采访过戛纳电影节,还担任过“一种注目”单元的评委。20世纪70年代以前,戛纳电影节的入选片都是由各国自选自送,也就是说,影迷们在戛纳看到的电影,真的是各国选送的本国最佳电影。当时的戛纳电影节还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电影盛会。但从70年代末期开始,戛纳电影节不再由各国选送电影,而是由电影节自己组成了一个选片班子来选片。于是,地下电影、反叛电影、反政权电影等所谓的“独立电影”就开始进入戛纳。很多在西方久居的中国人都有这种体验或印象,即西方人对日本人特别友善,对中国人则往往侧目而视。这与电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心者可以去电影资料馆探究下,多年来入选戛纳电影节的日本电影,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温情片,对日本社会充满善意的、温馨的、美好的描述,而中国,特别是大陆入选片则往往是完全相反的。
张艺谋1994年的《活着》在戛纳得了大奖,但是他1999年将《一个都不能少》送去时,就被戛纳拒绝了,张艺谋为此发了公开信。此后,张艺谋再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入选戛纳正式参赛单元。
中国也应该成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者和讲解员
读+: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西方?又该如何树立起中国人的自信?
郑若麟:西方是一个真正的复杂体。我们可以从西方学到很多有益的东西,西方文明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一面,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对人类造成无数悲剧。我们要在思想上树立起中华文明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要学会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和尊严。当然,这不是要盲目地排外,也不是盲目地全盘接收,我们要掌握一个度,要心中有数。
我们面对外来精神的时候,首先要了解它、理解它、参透它,随后我们才能知道其对于我们的利弊,而如果我们对外界一无所知的话,一旦我们与外界接触,我们就会变成精神上“不设防”的愚民。所以我主张强化我们的对外交流,我力主我们的年轻一代,要走遍世界,要行千里路、读万卷书,还要察万宗事。
我们要重温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怀疑一切。我们要多想。
要了解世界,读书读史是重要的方式,但外国学术作品最好是读原文。读西方的书,一定要注意区分哪些是西方希望我们阅读并接受的,哪些是他们不希望我们阅读甚至不希望我们了解的作者和著作,如果我们只知道照着西方给的书单子去读书的话,那么越读就越会陷入西方为我们预设的道路而无法自拔。
除了读书读史,还要多多旅行,包括在国内的旅行,也包括我们到世界去看看。不仅仅要看发达国家,也应该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开放、进一步走出国门。
中华文明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在漫长的5000年中华文明史中,我们不到200年的挫折,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而已。多难兴邦,历史上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宛如大浪淘沙,它冲走的是精神上的弱者和失败者,它将重塑的是我们的灵魂。中国不仅仅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且也应该成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者和讲解员。
【编辑:李尔静 朱曦东】
一周热门
- {{index+1}}{{item.tit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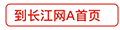

 互动
互动
 投诉建议
投诉建议 长江头条
长江头条 在线问答
在线问答 数字报
数字报
 移动端
移动端
 长江网移动端
长江网移动端 长江头条移动端
长江头条移动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