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学
前不久,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做客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以《何问西东:文明的对话与回想》为题,分享了他对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看法,线上线下24万多读者参与。
张国刚曾入选清华大学“985百人计划”、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计划。1989—1998年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此后担任过汉堡大学、剑桥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特里尔大学教授;历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张国刚的代表作之一《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去年获评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由他主讲的《中西文化关系史》被评为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讲座结束后,他接受了本报《读+》专访。

张国刚做客“长江讲坛”。记者何晓刚 摄
如果郑和过了好望角
“继续向前走!”印度洋上,郑和作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驶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历史从此改写。
1998年,还没有成名的刘慈欣写过一篇架空小说《西洋》,开头就是这个场景。然后他笔锋一转——到20世纪,中国才是“日不落帝国”,华夏文化拥有世界文明霸权……当然啦,这首先要归功于郑和船队过了好望角、进入西欧、想抄近路回家于是发现美洲。
在刘慈欣之后,一大批作者进行过这种架空、穿越,他们回到宋朝、明朝乃至清朝,试图带去工业和科技的元素,最终改变历史走向。
的确,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有过一些令人扼腕的瞬间。比如甘英止步于中东,汉朝没能和罗马握手;再比如郑和的条件比晚于他近百年的哥伦布强得太多,似乎也有机会作出超过哥伦布的功业。
可是,读过张国刚的《胡天汉月映西洋》就会明白,郑和纵然是过了好望角,获得了一些什么,历史进程也不会有多少改变。
获得知识?郑和之后一百多年,传教士把西方人花了无数血汗和金钱弄到的地理大发现知识写成书、绘成图,在中国公开印刷发行,并且带来了南北极、经纬度、寒热带以及冰川、地心等概念,但是没有引起国人“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的反应。
获得技术?南怀仁在中国制造了566门大炮,在历次战争中立功,他也写了书,讲述造炮和瞄准之法。战争结束后,炮术就和传教士们制作的钟表、测算的天文一样,成为皇室的玩物,束之高阁;没有人去关心背后的物理化学数学机械冶金,更没有人警惕这些玩意儿背后的工业生产力和超大势力。
获得财富和土地?中国连周边国家的土地都没有掠夺,更不可能去非洲殖民。明朝对外贸易赚钱很多,长期出超,这些白银没能转化为工业资本,变成了财主们的储藏。
没人对利玛窦的长相感兴趣
事实上,根据《胡天汉月映西洋》所述,假如郑和过了好望角,他最有可能遇上的是葡萄牙亨利王子的船队。
亨利王子比郑和年轻20岁,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远离首都,在葡萄牙一个海角边陲小镇度过。在这里,他创建了地理硏究院、航海学院、天文台以及收藏地图和手稿的图书档案馆,网罗了各国的地理、天文、制图、数学专家。他自任航海学院校长,还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前往西非海岸的航海探险,不断搜集航海资料,详细记录海潮、风向、鱼和海鸟的运动,改进造船、制图和航海技术。
郑和船队的规模以及航行里程的长度,可谓世界上空前的壮举。亨利王子的航海活动则包含着精明的算计、科学的热情和经济的追求,他不仅研究科学,同时还建殖民地、贩黑奴。如果两支船队开战,郑和很有可能先胜后败,他每次出行都花掉大笔钱财,厚往薄来,对国库是沉重负担,亨利王子却能“以战养战”。
同样的航海,不一样的结局。这就是历史的悖论。“恶”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郑和的航海结束了,明朝的航海事业就结束了;亨利王子去世后,他的航海学校却培养出更多的探险家。
《胡天汉月映西洋》里,不乏这种“冷知识”,以及由冷知识引发的冷思考。比如,张国刚发现,利玛窦在中国广泛结交官僚和知识分子,这些人都乐于描述利玛窦“通中国语”,“入中华未甚久而儒服汉语,楚楚佳士”,努力效仿中国衣冠礼仪,负笈十万里观光上国并热心学习中华文化,云云;另一方面,只有两个人在记录里描述过利玛窦的长相。
不去考究这位外国朋友的背景、经历和心理,从而获得新知、了解世界,只是津津乐道于其人如何服膺我天朝上国的文化,这种文化现象并不陌生啊!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其实源于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空间上有多条通道,时间上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张国刚从古印欧人的迁徙写起,一直写到鸦片战争以前,这广袤时空中的东西方交流碰撞,其实都发生于丝路和海上丝路。他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人类最重要的具有源头性的四大文明中,其他三大文明都位于中国的西部,他们都具有某种共同的历史、宗教、语言、战争方面的联系,对他们来说,中国文明是真正具有独特性的“他者”。
身处这样的世界,中国人必须更加勇敢、更加开放,同时更加审慎,更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张国刚认为,“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就是这种情况下对于全球化的中国回应,“一带一路”不仅是传统丝路文明在现代的延伸,而且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和纽带。

《胡天汉月映西洋》张国刚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访谈】
古代出西域多是政治军事考量
读+:在“丝绸之路”上,中国人是主角吗?
张国刚:中国更多的是起一个“供给方”的作用,提供商品,也提供了中国控制区域一侧的秩序和安全。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主要是边境贸易,中国人主动出境贸易不占主流。根据文献记载,陆上丝绸之路,担当东西贸易的商人,主要是塞种人,即大月氏人、匈奴人,中古时期则以粟特人为主流。唐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还有部分犹太人,华人也有参与。《法显传》提到,法显从斯里兰卡返回中国的途中,就是因为中国商人对他的保护,才免于同船婆罗门商人的戕害。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的原因,也由于中国政府对外贸的严格管控,华人参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多半是散兵游勇式的,其规模不能与胡商相提并论。据阿拉伯文献记载,9世纪的广州,已经有数万名外商居住。
读+:为什么与西方相比,历史上的中原政权在东西方交流方面显得不够主动进取?
张国刚:除了大家熟悉的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之外,应该说还是有一些主动进取的行为。比如战国时期的赵国就强调过,与西域的交通不能被切断,否则就会影响到胡马、代犬、玉石等物资的进入。再比如隋炀帝也曾经大力经营西域,他其实是中国皇帝中走得最西的一位;此外唐德宗时期(约785年),大臣杨良瑶奉命从海上出使大食,比郑和早七百年,可能有些读者尚不知道这件事。
东西方交流涉及“动力机制”问题。
无论是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前138 年),还是东汉和帝时期西域地方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无论是唐德宗派杨良瑶海路西行,还是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 年),都是出于政治和外交交往的目的,带有军事性质。
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二个维度是经济与财政需求,第三个维度是科技对于丝路交往的重大促进作用,第四个维度是宗教热情和知识追求。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郑和下西洋是为执行对外政策,而非欧洲大航海那样为资本原始积累服务。当帝王在经济上足以应付巨大开支时,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就会产生积极向海外拓展的雄心伟志。
而当这种政治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或经济上因开支浩繁而难以承担时,帝王自然会缺乏积极进取的热情。
如果郑和航海也如欧洲那样,不单纯是以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致力于为一个有足够独立性的资产阶级开辟广阔的海外市场,那么就会有持续的动力和经济援助支持这样的远航运动继续发展下去。可以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决定了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事业只能是昙花一现。
中国巨大的经济实力是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
读+:明清之际,传教士们来到中国,与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结交,带来了最新的地理和科学知识,讲述了西方国家和社会的一些情况,为什么没有引起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足够反响?
张国刚:总体上,西方科技在明清时期未能发挥重大作用的基本原因在中国社会的疑忌、排斥以及不能放弃自身文化的优越感。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怎么相信,把新知当成“志怪”和谈资;另一种则是把传教士们所说附会到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比如把地理大发现、全球几大洲的概念,附会到了战国时代邹衍的“九州”说。邹衍认为在中国赤县神州这个小九州以外,还有另外八个和九州相同的州,即中九州,在中九州以外,还有另外八个和中九州相同的州,即大九州,等等。
客观地说,这种“古已有之”、把外来新事物和本国传统联系起来的办法,是面对文化冲击时常用的策略。比如,王阳明的“心学”受佛教启发,但是他将其联系到庄子身上;再比如,佛教刚传入中国时,知识界也是拿出庄子来。
面对传教士们在天文历法方面明显的优势,明末遗民首倡、康熙皇帝与数学家梅文鼎互相迎合的天文历法领域的“西学中源”说成为中国士人维持文化自尊心的一剂良药,但这种穿凿附会的解说和无视事实的自我陶醉,就学术而言毫无积极意义。“西学中源”是一种根本上错误的看法,因为这种逻辑导向是不必再钻研与吸收西学,更谈不上深层次考虑中西两种文化的异同与发展。这样一种认识在思想界长期盘踞,造成的恶果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中国士人,读经、科举、做官,其人生轨迹是平稳而封闭的,没能“睁眼看世界”。
读+:中国在东西方文明交往方面,有哪些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
张国刚:回顾这段历史,从根本上说,中国巨大的经济实力是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巨大的经济能量也是中国在中西交往中的优势。问题是,公元1500年以后,欧洲人东来,明清王朝开始直接面对西方,没有了东南亚和波斯人、阿拉伯人的中间商,明清王朝反而局促不安起来。或者说,没有政治上的互信,明清王朝对于直接与陌生的欧洲人做生意,满腹狐疑。
18、19世纪的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体系,欧洲人也没有任何奇珍异宝,可以平衡中国在丝绸、瓷器、茶叶等对外贸易的巨额出超。于是,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的金融秩序,朝廷财政严重依赖白银进口,中国东南地区的产业分工甚至也依赖上了对外贸易。这是汉唐时期所不曾有过的。
于是,当欧洲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时,经济贸易演变成了政治和军事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鸦片战争到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发现建立政治上的互信,军事上要有自我保护能力,要有拳头产品,很好地处理经济贸易和金融问题,这些历史的经验,对于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仍然不无启发意义。(记者李煦)
【编辑:李尔静 毕婷】
一周热门
- {{index+1}}{{item.tit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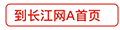

 互动
互动
 投诉建议
投诉建议 长江头条
长江头条 在线问答
在线问答 数字报
数字报
 移动端
移动端
 长江网移动端
长江网移动端 长江头条移动端
长江头条移动端